
最近在网上@ 看客inSight看到一篇加拿大华人写的文章,深有感触,分享给大家,希望每个人都能用心体会生命!
完善的临终服务,没有让照护者放弃吃苦
在死亡面前,如何保有人的尊严?现代医疗是帮人活下去,还是害人死不了?
这些疑问不仅摆在需要直面死亡的病人眼前,更盘旋在照护、陪伴病人的家属心里。
陪伴亲人走向死亡的过程,总是挣扎痛苦的。在常见的叙事里,亏欠亲人或放弃自我是一道单选题,人正常的生活注定因此被剥夺。
生活在加拿大的林舟,在经历了几位亲人的离世后,抱着这些疑问,走进了所在社区的临终关怀中心,成为一名志愿者,重新思考临终关怀的意义。
在加拿大,更加完善的临终关怀服务释放了家属照护上的压力,帮助他们更好地平衡爱、责任与自己的生活秩序。
但这里的华裔家庭们,却依然没能从沉重的道德枷锁中解脱出来。
在加拿大做临终关怀
我从小就想从事医护相关的工作,小时候读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医学相关的那几章我翻得最多,可惜学业工作都和这个行业八竿子打不着。
大学时我出了国,现在留在加拿大工作,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有一次亲子社区活动,我听另一位妈妈说她在临终关怀机构工作,机构里住的都是生命已经走到末期的人,所有医疗手段以缓解痛苦为目的,而非延长生命,为的是让他们能更舒适地度过临终,不留遗憾地走完人生。
听说机构需要很多志愿者提供支持和陪伴,我心里有点蠢蠢欲动,儿时的兴趣又重新被点燃。
更重要的是,当时我和丈夫身边的几位亲属先后患癌离世。生命的临终阶段究竟是怎样的、家人要如何度过这段时间,探索这些对我而言有了更深刻的意义。
去年二月初,我联系到临终关怀中心,经历了一连串的面试和材料填写,又完成了三个月的培训。从八月份起,我正式开始了志愿者工作,一直持续到今天。
去当志愿者之前,我抱着一种向往的心态,以为加拿大的临终关怀已经十分先进。
深入了解后发现,其实当地人对此还是有很多不理解。尤其我所在的社区意大利人比较多,他们的家庭观念和中国人一样很重,在家或者医院照护仍然是第一选择,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临终关怀。
但整体而言,加拿大的临终关怀理念还是更加普及,运作系统也相对完善。
在加拿大的医疗体系里,除了负责给出诊断的医生,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社工积极介入,为病人普及临终关怀的理念,提供社会层面的支持。
临终关怀在这里是公共事业,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政府拨款和慈善捐赠。据我所知,是不会对病人或住户收取费用的。
当一位社区居民被诊断为患有终末期疾病(Terminal illness),即现有医疗条件无法解除疾病、预期寿命较短时,有几种选择方案,临终关怀就是选项之一。又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,可以申请不同的服务:
无法医治但又需要医疗器械辅助,很难回家的患者,可以就地入住医院的临终关怀部。情况稍好、不需要大量护理,则可以申请社区内上门的临终关怀服务。
最后一种,就是我所在的住家型临终关怀中心。这类中心有24小时的值班护士和护工照料,还有兼职的心理咨询师和音乐治疗师。
中心的居住环境很好,都是面积较大的单人间。房间里有独卫,一张床有小双人床那么大,也只占了这个房间的不到四分之一。但床位较少,只有12个床位,一般会提供给生命期限不超过3个月的患者。
住户入住后,护士会向家属讲解临终关怀的理念,和人在临终时可能会有的反应。比如肢体末端的皮肤开始偏蓝紫色、喉咙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。
哪些征兆是正常的临终表现,哪些则需要护士干预,对于家属而言,这些讲解能缓解他们对于眼下未知状况的恐惧感。
因为有自己的全职工作,我每两周的周末去一次中心。志愿者的工作内容不固定,核心就是为有需求的住户和家属提供帮助。
我最常做的是巡房,了解每个住户的状态。人患病到临终时会比较难受,脚会抽搐、发抖,有人会很烦躁,想要扯东西或者不停翻身。我看到了就会叫护士,酌情给一些镇定或者止痛的药物。
住户会签禁止心脏复苏协议(DNR:do-not-resuscitate order),也叫“尊严死亡”。因此除了安全,中心不会对住户有任何要求。
有一位心脏衰竭的意大利奶奶,白发梳得整齐,指甲染了鲜艳的亮红色。她只愿意吃冰激凌,吃药的时候很抗拒,我就坐在旁边一口药、一口冰激凌地慢慢哄她吃完。
“哦,Bella(意大利语:小姑娘),我真的特别喜欢你。”她有时候停下来拉着我的手,一张张把病房里的照片指给我看,说下回来要给我涂指甲,想要和我一起跳舞。
还有的住户已经不能进食,但又很想吃某种东西,我们就会拿食物在嘴唇上沾一沾,分享香气和味道。
在临终关怀中心,人本身的优先级始终大于疾病。
拧巴的华裔家庭
在移民国家加拿大,临终关怀中心里能见到各种族裔。或许是因为共同的文化背景,华裔住户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。
临终关怀中心全天都会有两位护士、一位护工和一位医生,白天还有志愿者。志愿者里一部分是来积累经验的医护行业学生,还有一部分因为家人受到过此类帮助,自愿回馈社区。他们都专业且负责,足以把住户照顾得很好。
西方家庭也普遍更愿意把照护工作交给他们。有经济能力的还会额外花钱雇佣护工到中心来,专门看护处于终末期的家人。
很多西方家庭选择临终关怀,是想让自己摆脱照护压力,回到儿女、夫妻、兄弟姐妹的身份,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为临终的家人提供情感陪伴。他们与中心的工作人员是互补合作的关系。
然而在这里快一年,我从来没有见到能摆脱照护束缚的华裔家庭。他们不会额外请护工,也不放手让中心自己的护工来照顾,心理上总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家属们会轮班陪床,抢着承担大部分照护工作,更像护工的“竞争者”。
中心里有一位越南家庭的父亲,是广东那边过去的。聊天的时候,女儿跟我说:你看,那些西方人都把爸妈丢在这里不管,我们中国人永远都是会照顾爸爸妈妈的。
他们家四个兄弟姐妹,都已经成家立业。妈妈身患老年病,在养老院七年,现在父亲也倒下了。这段时间,四个人在工作、孩子、妈妈、爸爸四边周转,都情绪紧绷,即使是在父亲床前,争吵也常常发生。
华裔家庭对这种“必须亲自照顾家人”的传统感到骄傲,可我看出每个人都在崩溃边缘。
更拧巴的在于,家属们放不下照护的重担,又很难把患者照顾得更好。
最近有一家中国人入住了中心,老爷子患病,他的太太一直陪在身边照护,两个人都不太会讲英语。女儿有工作在身,平常来得不多。
中心的每个住户房间里有一张椅子,拉开就变成一张窄床,她每天就睡这儿。人到临终阶段常会失去对白天黑夜的感知,她的丈夫经常半夜醒来,发出声音或者提各种要求。
单独聊天的时候我追问好几次,她才坦言自己睡不好,晚上最多合眼三四个小时,“他晚上一直闹。”
照顾患者带来的疲惫是必然的。其他家属也会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吐苦水,但如果发现自己压力过大,他们会选择干脆暂时放下照护的担子,通过其他方法排解。
可在华裔家庭里,大多数家属既不愿意开口和志愿者这些“外人”倾诉,也不愿意放下照护责任哪怕一秒。时间长了,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不免会流向被照护者。
上次我去中心,太太看到我来了,终于松了口气,但脸色还是很差。我提议由我陪着先生,她可以先去洗个脸吃点东西,稍微休息一会儿。
她断然拒绝了,但留在房间里也是神色恹恹,肉眼可见地不高兴。“你看你在这多舒服,躺这么大张床,饭都给你喂到嘴边儿。”看见老爷爷醒了,她半开玩笑地抱怨,“我只能睡那么窄一个躺椅,翻身都翻不了。”
那时候她丈夫已经处于很末期的阶段了,几乎是皮包骨,吃不下什么东西。我听到这些话,心里一开始觉得很不舒服。
可她紧接着又说,但是你放心,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不会走的,我永远都在这。
我站在旁边听,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或许忙碌起来就能逃避亲人即将离世的事实,或许在他们的世界里,吃更多苦就代表更多爱,代表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。
但当家属照顾不好自己时,被照护者的需求也容易被忽视。
有次我进房间和这位老爷爷打完招呼,他还一直颤颤巍巍地伸着手。不知道他想要什么,我就牵住他的手,任凭自己的手被带到下腹部的位置。我没明白他哪不舒服,就一直问,是这里不舒服吗?需要揉吗?
“哎呀,你不要拉着人家年轻小姑娘老往自己身上拽!”太太不好意思地跑过来,她把丈夫的手压回到被子上,安抚地拍了拍,“没事你就好好睡,别闹腾。”
我观察他的表情还是不舒服,就叫护工来换洗擦身,顺便看看情况。护工换纸尿裤的时候一看,原来他一直躺在床上,尾骨被压着已经生了褥疮,那一片都黑掉了。
看着他尾骨已经蚀出了一个洞,我难免心里会有些评判,但更多的是伤感和无奈。
中心一直是住户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,如果家属一直陪床,有强烈的自己照顾的意愿,护工相对就不会频繁地干预检查,而是更多去照看没有家属照顾的住户。
他的太太后来也说,幸好我今天过来了,不然还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在闹什么。“尾巴骨上都有个洞了,那肯定难受,对吧?”听着也很心疼。
我其实能够理解他的太太。不分昼夜地应付患者的各种症状,每天吃不好、睡不好,是没有心力像两周才来一次的我这样,不厌其烦地探索他的每一个反应的。
易地而处,我未必做得比她好。可如果她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,让志愿者或者护工搭把手,也许就能发现得更加及时。
照护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日常。很多人会觉得我多辛苦一点、少睡一点、有情绪忍忍没什么,但是长此以往,照护者会和需要照顾的人一起消耗殆尽。
没有照片的房间
不同文化背景的人,对于生命临终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别。
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是,在华裔住户的房间里我没有见到过照片,甚至想不起来有什么与住户个性相关的物品。
西方人的房间里总是有很多照片,住户们还会带自己喜欢的毯子、钟爱的装饰画。有一位老爷爷特别喜欢鹿,那段时间正好圣诞节,外面摆了很多鹿的装饰灯,他的家里人就把灯饰一股脑搬进房间,让他能一直看到。
华人住户我见过很多,他们的房间里会摆吃的、药、衣服、润肤露等生活用品,其他就没有了。
可人之所以是他自己,是因为他有独特的经历、想法、偏好和个性,当这些被“疾病”这座大山掩埋时,对于人的价值也是一种剥夺。
在其他族裔的家庭里,家人之间有很多个性化的情感交流。他们会有很多时间一起翻旧照片、读亲朋好友的留言,和住户一起挑选鲜花或者听几首他们喜欢的歌。
中心有一位讲波斯语的老奶奶,她的家人每次来都会帮她梳头。不是为了整齐,而是因为她很享受梳头的过程,这种行为让她觉得舒服。
而在华裔的住户家庭里,互动总是离不开最基本的生理需求。
有一家中国人,住户老爷子说话已经很困难了,大儿子和小儿子两个人轮流忙着喂水喂汤。喂了两口,老爷子就打手势示意够了。
房间里沉默一会儿,过几分钟,儿子们又问要不要喝。看老爷子不反对,再喂两口,再被喊停,循环往复。
我试着和两个儿子聊天,套出老爷子爱听老歌、爱看抗日剧。一首草原情歌在房间里一放,老爷子突然睁开眼大声说了一句方言,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如此清晰地讲话。儿子说,这是喜欢听的意思。
关系亲密的家人,往往更了解住户独特的心理需求。但在华裔家庭,家人总在做护工的工作。
你吃不吃这个?你要不要上厕所?我给你翻个身?这是我在所有华裔家庭的房间里听到最多的问题。无论是照护者还是被照护者,“高兴”“享受”是件很少被考虑的事。
好像在生命走向尾声时,人会坍缩成最为原始的动物态,值得做的只有继续活下去本身。
我接触到的华裔家庭们,似乎从住进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在上演落幕。但要真说起来,他们却是最不愿意接受死亡的。
其实住进临终关怀中心,治愈已经没有希望,也不是临终关怀的目的。但华裔家庭的照护者们还是会常劝患者,你要多吃点,多吃点才有力气,多吃点才能好起来。
每当这些时候,那种别扭又无措的心情、沉重的不甘心,总会令我想起自己国内的家人们,和他们面临过的生与死。
离开的人,留下的人
这几年,我和丈夫的父母已经开始承担起照护者的角色,面对他们因病痛或衰老,走到了生命临终阶段的亲人。
2014年,我婆婆的母亲在家摔倒,脑部大面积出血,出血的位置压迫到了负责睡眠的区域,她感知不到困意,始终无法入眠,很痛苦。而且无法开刀,只能靠插管输送营养液来维系生命体征。
姥姥一生都是个活力四射、特别要强的人,这样干耗着苟延残喘的处境,对她而言不能更加残忍了。虽然家里最后一致决定拔管,但过程中也因为犹豫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治疗。
“是不是停止得太晚了,是不是让妈妈多承受了无谓的痛苦?”
多年过去了,我和婆婆上次聊起这件事,她说自己有时候半夜醒来,还是会想当初做的决定到底对不对。
但这些只能在心里想,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。
在这之后,我就有了进一步了解临终关怀的念头。这项事业不仅关乎逝去的人,对留下来的人同样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。
2020年,丈夫的奶奶患癌,无法手术,也不适合治疗,只能在医院煎熬。当时国内临终关怀还不太普及,公公不太能接受这种理念,当地也没有找到有条件的机构,奶奶的最后一段时光还是留在了医院。
直到最后,尊重奶奶的意愿,她才得以在家中离开。
后来丈夫的姑妈患上癌症,当时虽然也没有接受专业临终关怀的条件,但回想起奶奶的经历,公公也意识到,在临终阶段,人的感受和需求才是最重要的。
有一段时间姑妈吃不下东西,只想吃冰棒。公公在天寒地冻的一月份跑了十几家小卖部,买下了能买到的所有存货,让她每天都能吃上冰棒。到了最后,他坐在姑妈床边陪着她,牵着她的手说:你放心,这边我们都会照顾好的。
她平静地离开了我们,到今天公公已经可以微笑着提起她。
当时我还没有成为中心的志愿者,但我觉得公公所做的其实就是临终关怀。建立一套完整的临终关怀系统需要更多时间,但最有价值的、能超越时间的是理念本身。
从这个视角来看,在国内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照护方式也值得更多的讨论。
我的爷爷晚年也罹患癌症,全家都对病情守口如瓶,住院检查和照护一直由我妈陪同。处在这样的环境中,老人自然有所察觉,常常会问我妈自己到底怎么了,是不是“快要死了 ”。
知道这件事之后,我总觉得应该告诉爷爷,毕竟这是他的人生,他有权决定如何度过这一段时间。但我妈的态度很坚决,就是瞒着他,劝他不要多想、配合治疗。
“你不懂的,你爷爷特别胆小。”他知道了会崩溃的,妈妈对此很笃定。
我试探着说过两次,后来没有再提。毕竟照顾爷爷是由我妈一力承担,我没资格多说什么。家人直到最后也没有说出实情,但我始终不太赞同这样的做法。
我们总是在乎能否治愈、能否延续,但生命的长度不是它唯一的价值。在人生的每分每秒,人的自主权和感受本身都时刻重要。
直到今天,我都记得自己被邀请参加的那次葬礼。主人公是我第一天来中心就见到的住户,也是我在那儿见过最年轻的病人,只有38岁。
她是家里的长姐,也是家族里第一个面对死亡的人。
在葬礼上,她的弟弟最后致辞说,他们很幸运,能在临终关怀中心陪姐姐度过了最后的日子,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。他们学会了及时表达爱、说抱歉,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明天,有下一秒钟,“这是她留给我们的礼物。”
在临终关怀中心,离别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尾。我讲述他们每个人的故事,也是他们活在我生命中的方式。每次我想到他们,就想到我可以如何看待照护,如何理解临终、面对生命。
这也是他们留给我的礼物。
阅读原文,侵删
封面:🆓 Use at your Ease 👌🏼 from Pixabay
君君提示:你也可以写原创长文章,点此查看详情 >>
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本人和加拿大省钱快报共同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。长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,如有更多内容分享或是对文中观点有不同见解,省钱快报欢迎您的投稿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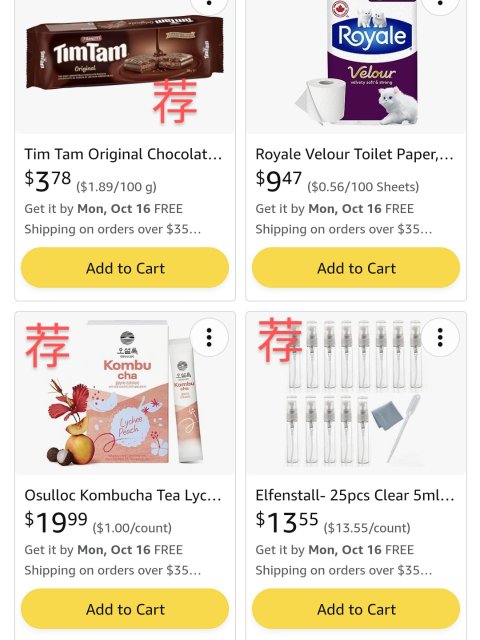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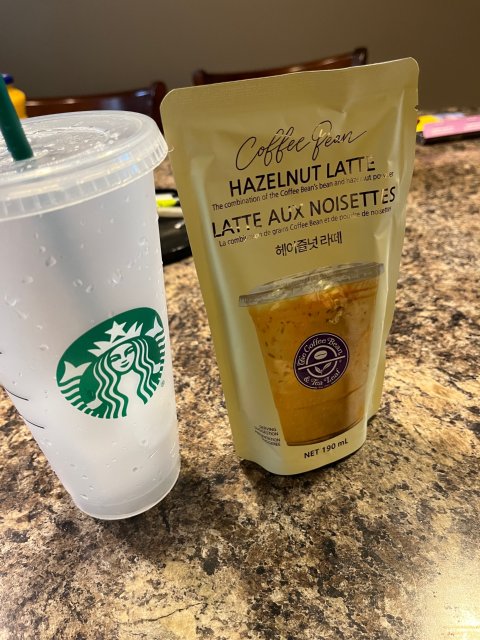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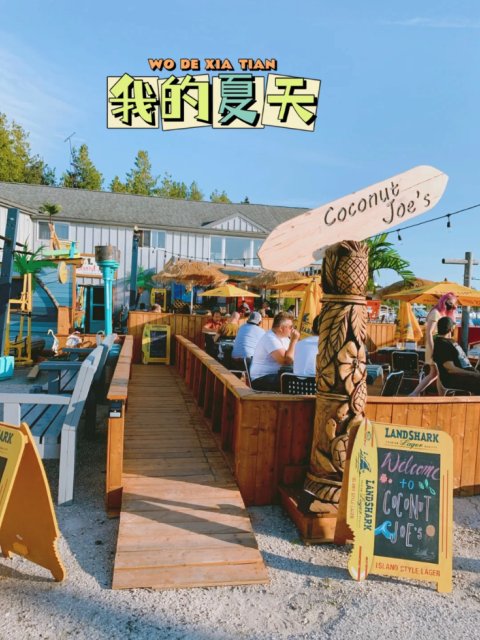

最新评论 2
:每个人成长的年代 经历 环境 很多很多都不一样,怎么做都没有什么好的坏的,站在每个人的角度看也都各有不同。都是自己选的
:真的很怕看到那种互相拖累的境地